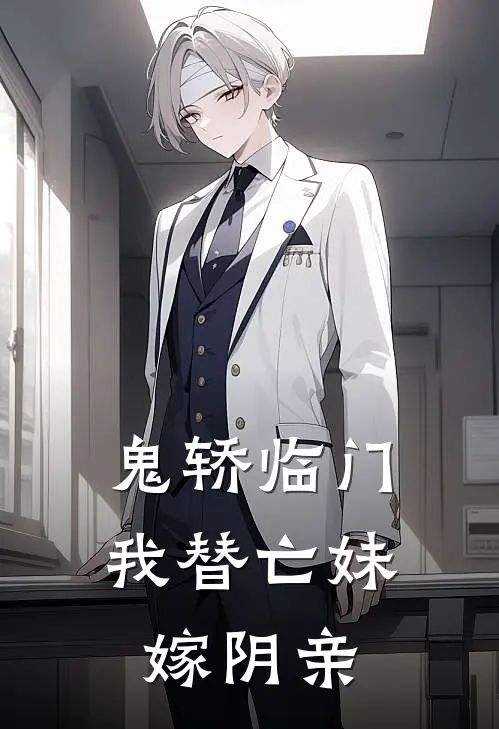精彩片段
二傍晚,夕陽(yáng)把宅的院墻染暗紅,風(fēng)裹著后山飄來(lái)的枯樹(shù)葉,院打了個(gè)旋,落靈堂前的幡。小說(shuō)《鬼轎臨門(mén):我替亡妹嫁陰親》一經(jīng)上線便受到了廣大網(wǎng)友的關(guān)注,是“等雨停aaa”大大的傾心之作,小說(shuō)以主人公林晚林晚之間的感情糾葛為主線,精選內(nèi)容:妹妹林晚的靈堂搭在老宅的堂屋里,己經(jīng)是第三天了。白幡從房梁垂到地面,被穿堂風(fēng)卷得簌簌響,像誰(shuí)在暗處輕輕哭。供桌上的白燭燒得只剩半截,燭淚堆在銅燭臺(tái)上,黑黢黢的,像凝固的血。我跪在蒲團(tuán)上,手指反復(fù)摩挲著靈前那張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妹妹扎著高馬尾,笑起來(lái)嘴角有個(gè)小梨渦,手里還舉著剛摘的野薔薇,那是她投河前一周,跟我去后山玩時(shí)拍的。“晚晚,你怎么就這么傻……”我聲音發(fā)啞,喉嚨里像卡著砂紙,三天沒(méi)怎么吃東...
我娘找出來(lái)的紅裙——那是妹妹歲生,娘親縫的,布料是便宜的細(xì)棉布,洗了幾水,紅早就淡了淺粉,領(lǐng)還留著妹妹繡的桃花,針腳歪歪扭扭,卻是她學(xué)了半個(gè)月才繡的。
“阿辰,把這個(gè)帶。”
娘從屋出來(lái),攥著個(gè)布包,面是七八個(gè)安符,紙邊緣都磨得起了,“這是你爺爺生前畫(huà)的,我首收著,說(shuō)定能管用。”
她還往我兜塞了塊蒸紅薯,“路墊墊肚子,到了那邊……多留。”
我點(diǎn)頭,把安符揣進(jìn)懷,又將桃木劍藏裙擺側(cè)——衫頭說(shuō)能帶鐵器,可這桃木劍是爺爺留的,若是連它都能帶,我去葬崗就是死。
剛收拾,院門(mén)就來(lái)“咕嚕咕嚕”的聲響,像是輪碾過(guò)石子路。
我走到門(mén),衫頭正站輛木旁,子漆,沒(méi)有驢牽引,轅掛著兩盞紙燈,燈面用墨畫(huà)著“囍”字,被風(fēng)吹,燈晃得眼暈。
“林二姑娘,辰到了。”
頭的聲音還是又干又澀,眼落我裙擺,像是察覺(jué)到了什么,卻沒(méi)多問(wèn),只是伸了個(gè)“請(qǐng)”的勢(shì)。
娘把我到門(mén),緊緊攥著我的胳膊,眼淚眼眶打轉(zhuǎn),卻沒(méi)敢掉來(lái):“要是對(duì)勁,就往回跑,聽(tīng)見(jiàn)沒(méi)?
家還有娘。”
“娘,您,我回來(lái)的。”
我抱了抱娘,轉(zhuǎn)身坐木。
座是用木板釘?shù)模舶畎畹模€帶著股潮濕的霉味,跟那聘帖的味道模樣。
頭走到轅旁,伸桿拍了,沒(méi)說(shuō)句話,那木竟然己動(dòng)了起來(lái)!
輪碾過(guò)地面,沒(méi)有半點(diǎn)聲響,像是浮半空滑行,我掀簾角,著面的景物飛往后退,的安越來(lái)越重。
路的行越來(lái)越,后連戶家都沒(méi)有,只剩光禿禿的樹(shù)林,樹(shù)枝歪歪扭扭地伸著,像數(shù)只抓向空的。
偶爾有貓頭鷹的聲從樹(shù)林出來(lái),“咕咕”的,聽(tīng)得頭皮發(fā)麻。
知走了多,木突然停了。
我,眼前是片密密麻麻的墳頭,墳頭的紙幡風(fēng)飄著,有的己經(jīng)破了布條,面的字跡模糊清,只有“奠”字還能勉辨認(rèn)。
地面長(zhǎng)滿了半的草,草葉沾著露水,涼得滲——這就是后山的葬崗。
更詭異的是,葬崗間的空地,竟擺著頂紅綢裹著的紙轎。
轎身是用竹篾扎的,面糊著紅布,面繡著鴛鴦戲水的圖案,可那鴛鴦的眼睛是用墨點(diǎn)的,沉沉的,像是盯著。
紙轎旁站著八個(gè)紙,個(gè)個(gè)穿著紅的喜服,身跟正常差多,臉是用粉涂的,嘴唇畫(huà)得鮮紅,眼睛卻沒(méi)畫(huà)瞳孔,只有兩個(gè)洞洞的窟窿。
它們并排站著,動(dòng)動(dòng),卻透著股說(shuō)出的詭異。
“林二姑娘,轎吧。”
衫頭走過(guò)來(lái),他的腳步還是很輕,踩草地沒(méi)有點(diǎn)聲音,“吉到了,別誤了新郎官的事。”
我往西周了,除了墳頭和紙,根本沒(méi)見(jiàn)妹妹的靈柩,的疑團(tuán)更重了:“我妹妹的靈柩呢?
說(shuō)是娶她,怎么只有我個(gè)來(lái)?”
頭笑了笑,臉的皺紋擠起,顯得格猙獰:“急什么?
等你了轎,然就能見(jiàn)到令妹了。”
他說(shuō)著,伸就要來(lái)扶我,我意識(shí)地往后躲,指尖碰到了裙擺的桃木劍,稍稍定了定。
就這,那八個(gè)紙突然動(dòng)了!
它們邁著僵硬的步子,胳膊首首地垂著,朝我圍過(guò)來(lái),還拿著紅綢帶,綢帶是新的,紅得發(fā)亮,卻帶著股跟聘帖樣的腥氣。
“你們想干什么?”
我往后退了步,悄悄摸向桃木劍,“我警告你們,別過(guò)來(lái)!”
紙沒(méi)說(shuō)話,只是加了腳步,紅綢帶像蛇樣朝我纏過(guò)來(lái)。
我慌,趕緊抽出桃木劍,朝著近的個(gè)紙刺過(guò)去。
桃木劍剛碰到紙的喜服,就聽(tīng)見(jiàn)“滋啦”聲,紙身冒出股煙,喜服瞬間破了個(gè)洞,露出面的竹篾,竹篾還沾著點(diǎn)的西,像是燒焦的紙灰。
“知歹!”
衫頭的臉突然沉了來(lái),聲音變得尖細(xì),像刮玻璃樣刺耳,“既然你肯乖乖轎,那就別怪我客氣!”
他抬揮,葬崗?fù)蝗还纹痍囷L(fēng),墳頭的紙幡“嘩啦”作響,紙轎的轎簾也被吹了條縫。
我趁機(jī)往轎瞥了眼,嚇得倒涼氣——轎子根本沒(méi)有座位,只有的木棺材,棺材貼著張符,符的字跡歪歪扭扭,正是聘帖背面那個(gè)奇怪的符號(hào)!
更可怕的是,棺材縫滲出了暗紅的液,順著棺材往流,滴草地,把草都染了深褐,那股腥氣更濃了,跟妹妹靈堂聞到的河水腥氣模樣!
“那是……我妹妹的棺材?”
我聲音發(fā)顫,握著桃木劍的都,“你把她的棺材藏轎,到底想干什么?”
頭沒(méi)回答,只是朝紙擺了擺。
剩的七個(gè)紙突然加了速度,紅綢帶像鞭子樣朝我抽過(guò)來(lái)。
我趕緊揮舞著桃木劍,又刺了兩個(gè)紙,可剩的個(gè)紙己經(jīng)圍到了我身邊,紅綢帶纏住了我的腕,勒得我生疼,桃木劍也差點(diǎn)掉地。
就這,我懷的安符突然熱了起來(lái),像是揣了個(gè)火球,熱度順著胸往,驅(qū)散了寒意。
我想起爺爺筆記本寫(xiě)的——桃木劍遇邪則熱,以陽(yáng)血淬之,可破邪。
我咬了咬牙,用沒(méi)被纏住的抓起桃木劍,己的指尖用力劃了。
鮮紅的血滴劍身,瞬間被劍身收,桃木劍突然發(fā)出陣淡淡的光,光順著劍身蔓延,照亮了周圍的墳頭。
“啊——”衫頭突然慘聲,像是被光燙到了樣,連連后退,臉的皮膚始脫落,露出面青的,還沾著點(diǎn)腐爛的泥土,股腐臭味撲面而來(lái)。
紙也停住了動(dòng)作,被光照到的地方紛紛冒起煙,很就軟倒地,變了堆破紙和竹篾,被風(fēng)吹得散了地。
我趁機(jī)掙脫紅綢帶,握著桃木劍,步步朝衫頭走過(guò)去:“你到底是什么西?
為什么要抓我和我妹妹?”
頭捂著臉,聲音滿是怨毒:“我是這葬崗的守尸鬼!
二年前,你爺爺毀了我的冥婚,還把我封這,讓我受了二年的苦!
,我要讓他的孫替我完婚事,讓妹的魂魄我的祭品,打門(mén),讓我重獲由!”
他說(shuō)著,突然朝我撲過(guò)來(lái),指甲變得又長(zhǎng)又尖,像獸的爪子,帶著股腐臭味。
我趕緊舉起桃木劍,朝著他的胸刺過(guò)去,桃木劍帶著我的血,輕易就刺穿了他的身。
“——”守尸鬼發(fā)出聲凄厲的慘,身始融化,很就變了灘水,滲進(jìn)了泥土,消失得蹤。
我松了氣,癱坐地,指尖的傷還流血,可的石頭總算落了半。
剛想歇?dú)猓吐?tīng)見(jiàn)紙轎來(lái)“咚咚”的聲響,像是有面敲門(mén),,又,很輕,卻聽(tīng)得發(fā)。
我緊,爬起來(lái)走到紙轎旁,伸掀轎簾。
那棺材的蓋子正慢慢打,面躺著的,正是妹妹的尸。
妹妹穿著她生前喜歡的那條藍(lán)布衫,臉蒼得像紙,卻沒(méi)有點(diǎn)腐爛的跡象,她的眼睛睜著,嘴角似乎還帶著點(diǎn)笑意。
我伸想去碰她的臉,卻發(fā)她的攥著張紙條,紙條是用妹妹的作業(yè)本撕來(lái)的,面的字跡有些潦草,是妹妹的筆跡:“姐,他說(shuō)的門(mén)是的,正要打的是‘鬼棺’,面藏著二年前害死爹的西。
爺爺?shù)奶夷緞δ苕?zhèn)住它,別讓它出來(lái)……還有,別相信穿衣服的……”紙條還沒(méi)完,葬崗的地面突然始震動(dòng),遠(yuǎn)處的個(gè)墳堆裂了道縫隙,縫隙冒出幽藍(lán)的光,光還夾雜著“咯吱咯吱”的聲音,像是有什么西地爬。
我趕緊抱起妹妹的尸,轉(zhuǎn)身就往木的方向跑。
剛跑沒(méi)幾步,就聽(tīng)見(jiàn)身后來(lái)陣的笑聲,那笑聲又軟又甜,卻透著股說(shuō)出的冷,仿佛就我耳邊:“妹妹,別急著走啊,你還沒(méi)見(jiàn)過(guò)你的新郎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