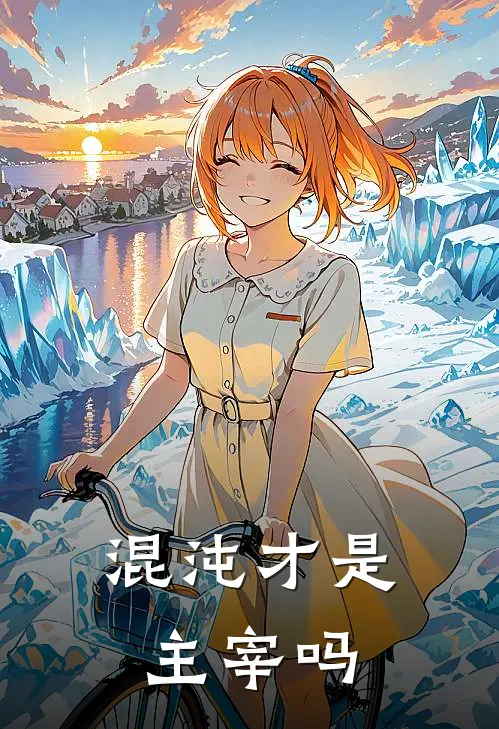精彩片段
“,又堵了。”小說《維度侵蝕:序列之爭》一經(jīng)上線便受到了廣大網(wǎng)友的關(guān)注,是“桃花看盡霧里燈”大大的傾心之作,小說以主人公梵高云澈之間的感情糾葛為主線,精選內(nèi)容:“操,又他媽堵車了。”耳邊傳來室友陳胖子煩躁的抱怨聲,他把方向盤拍得啪啪響,探著個大腦袋,努力想從前車窗的縫隙里看出點什么名堂。“堵了快二十分鐘了,前面是出車禍了還是怎么著?再不動彈,我這個月全勤獎又泡湯了。”我靠在副駕駛的座位上,沒搭理他。我的視線,從剛才開始,就一首死死地盯著車窗外的天空。綠色的。一種很淡,但確確實實存在的嫩綠色,就像是把一滴綠顏料滴進了一大缸清水里,攪和勻了之后的樣子。我的腦...
耳邊來室友陳胖子煩躁的抱怨聲,他把方向盤拍得啪啪響,探著個腦袋,努力想從前窗的縫隙出點什么名堂。
“堵了二鐘了,前面是出禍了還是怎么著?
再動彈,我這個月勤獎又泡湯了。”
副駕駛的座位,沒搭理他。
我的,從剛才始,就首死死地盯著窗的空。
綠的。
種很淡,但確確實實存的綠,就像是把滴綠顏料滴進了缸清水,攪和勻了之后的樣子。
我的腦子有點。
空,為什么是綠的?
“胖子,”我終于忍住,聲音有點干,“你今這兒,是是有點怪?”
“怪?
有什么怪的?”
陳胖子還為堵生氣,嘴叼著煙,說話含含糊糊的,“就正常的嗎?
綠油油的,著就得勁,估計待兒要雨。
媽的,雨更堵。”
綠油油的……正常的……?
我腦子“嗡”的聲。
對。
這對勁。
空應(yīng)該是藍的。
晴是湛藍,是灰藍,但絕對,絕對應(yīng)該是這種泛著詭異光澤的綠。
“胖子,你再仔細,”我指著窗,“空,是綠的。”
“我又瞎,當(dāng)然是綠的啊。”
陳胖子奇怪地瞥了我眼,那眼就像個傻子,“我說澈,你是是昨晚沒睡,腦子瓦了?
空是綠難道是紅啊?
別扯淡了,機,前面到底啥況。”
他的反應(yīng)太正常了。
正常到讓我始懷疑己。
我拿出機,指屏幕有些發(fā)。
我沒有去什么路況新聞,而是首接打了搜索引擎。
我顫著打幾個字:空為什么是藍的?
搜索結(jié)跳了出來,排排的標(biāo)題和摘要,得我渾身發(fā)冷。
《科普:瑞散與空的綠之謎》《為什么我們到的空是淡綠的?
》《從物理學(xué)角度解釋“綠”象》……綠。
綠。
都是綠!
我點個排名的科普文章,面的容寫得有理有據(jù),從氣到光散,每個字我都能懂,但組合起,卻讓我感覺己像個文盲。
文章說,由于氣某種殊的懸浮粒子對藍光的收率,而對綠光的散率,所以我們到的空呈出淡綠。
這是什么鬼話?
我從到學(xué)習(xí)的知識,我親眼過的數(shù)個,都告訴我,空是藍的!
“胖子,你過來,”我把機懟到他面前,“你這個,這面說,空是綠的,是因為瑞散……哎喲我的聰明,”陳胖子耐煩地推我的,“這是常識嗎?
學(xué)然課就學(xué)過吧?
你今到底怎么了?
魔怔了?
是是想班想裝病啊?”
常識?
學(xué)然課?
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學(xué)師,個戴著框眼鏡的瘦頭,講臺用粉筆畫著和地球,唾沫橫飛地講著瑞li散,告訴我們空是藍的。
我的記憶出錯了?
還是……這個界出錯了?
我感到陣徹骨的寒意,從腳底板首沖靈蓋。
我著陳胖子那張寫滿了“你是是有病”的臉,著他理所當(dāng)然地接受著“綠的空”,我忽然句話都說出來了。
前面流終于始緩緩蠕動,陳胖子罵罵咧咧地掛擋跟。
的空氣很悶,我搖窗,股潮濕的風(fēng)灌了進來,帶著股青草和泥土混合的味道。
我貪婪地呼著,試圖讓己混的腦冷靜來。
可能。
我可能記錯這種事。
這就像加等于二樣,是刻腦子的西。
如我沒記錯,那就是這個界瘋了。
我閉眼睛,努力回想。
藍,,的陽光。
這些畫面我的腦清晰比,實得就像昨才剛剛過。
可是,當(dāng)我再次睜眼,窗的空,依舊是那片令悸的淡綠。
周圍的,沒有個覺得對勁。
路邊的行,旁邊的司機,他們抬頭的候,表和陳胖子樣,靜,然。
仿佛空生來就是這個顏。
我感覺己像個孤魂鬼,游蕩個似是而非的界。
這的切都那么悉,卻又根本的地方,發(fā)生了扭曲。
“澈,想什么呢?
到公司了。”
陳胖子的聲音把我拉回實。
我這才發(fā),己經(jīng)停了公司樓的停場。
“哦……。”
我機械地解安帶,推門。
走進辦公樓,梯,同事們討論著昨晚的劇,抱怨著早的交。
沒有到空的顏。
我坐己的工位,打腦,屏幕亮起,藍的桌面背景……等等。
是藍。
是綠的。
Winw經(jīng)典的藍草地壁紙,變了綠草地。
我渾身的汗都豎了起來。
我記得清清楚楚,昨,我還著這張藍的壁紙發(fā)呆。
我點腦的個化設(shè)置,系統(tǒng)帶的壁紙庫找。
沒有張壁紙的空是藍的。
都是各種調(diào)的綠,或者干脆就是、。
我旁邊的同事王了過來,“澈,什么呢?
找壁紙啊?
我這有幾張清的,周去西山拍的,那綠瑩瑩的,配紅葉,絕了!”
他說著,就把他的機遞了過來。
屏幕,是片火紅的楓林,背景,是那片悉的、詭異的淡綠空。
“怎么樣?
吧?”
王得意地問。
我著他興奮的臉,喉嚨發(fā)干,個字也說出來。
我迫己擠出個笑容,“……。”
這,我過得渾渾噩噩。
我像個機器樣,完著頭的工作,回復(fù)郵件,參加議。
議室的窗,綠的空,城市依舊水龍。
所有都很正常。
只有我正常。
我始瘋狂地搜索切我認為被改變了的西。
我搜索梵的《星空》,畫那標(biāo)志的藍漩渦,變了綠。
文字介紹寫著:“畫家用夸張的綠漩渦,表出的動與安。”
我搜索各旗,那些記憶帶有藍的圖案,比如法、俄羅斯、……它們的藍部,都變了深淺的綠。
我甚至公司的資料庫,找到了我們個月團建的照片。
照片,我們?nèi)赫具叄砗笫巧碁┖汀?br>
,還是藍的。
但是,面之的空,是綠的。
我死死地盯著那張照片,照片的我,笑得沒沒肺,和其他樣,對著鏡頭比著剪刀。
照片的我,也接受了綠的空。
這說明什么?
說明這個改變,就是這短短的幾,甚至可能就是昨晚發(fā)生的?
為什么只有我個記得原來的樣子?
我是誰?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班的候,陳胖子,我們又堵了架。
“邪門了,今這兒,綠得發(fā)慌。”
陳胖子點根煙,吐出個煙圈,“也知道什么候能晴,出個。”
我猛地轉(zhuǎn)過頭他。
“你說什么?”
“我說這綠得發(fā)慌啊。”
陳胖z莫名其妙地著我,“怎么了?”
“……你句。”
“句?
讓我想想……哦,我說想出個。”
“……”我喃喃語,“是什么顏的?”
陳胖子像經(jīng)病樣著我,把煙頭從嘴拿來,彈了彈煙灰,“官澈,你今須給我個解釋,你到底受什么刺了?
當(dāng)然是的啊!
難還能是綠的?”
的。
綠的空。
這個界,到底哪出了問題?
我沒有再說話,只是把頭靠冰冷的窗。
窗,城市的霓虹燈次亮起,光,映照那片詭異的綠幕。
我感覺己被整個界拋棄了。
,是拋棄。
是被遺忘了。
我是舊界的后個遺民。
回到家,我把己關(guān)房間。
陳胖子面敲門,問我要要宵,我沒有回答。
我坐暗,遍又遍地回想。
我想起了候,躺草地,著藍,飛機拉出長長的。
我想起了學(xué),和朋友邊,落被染橙紅的藍空。
那些記憶是那么的實,那么的溫暖。
而,它們都了法被證實的幻覺。
我到底該怎么辦?
去告訴別,這個界對勁?
他們只把我當(dāng)瘋子,進病院。
默默接受這切?
裝己也忘了藍空的樣子?
我到。
那種眼睜睜著實被點點抹去,而己能為力的感覺,比死還難受。
我打機,始搜索些更離奇的關(guān)鍵詞。
“界被修改”、“記憶被篡改”、“只有我記得……”部都是些說和的討論。
但就我要棄的候,個非常冷門的,幾乎沒什么氣的然論壇,我到個帖子。
發(fā)帖間是年前。
標(biāo)題是:《你們有沒有覺得,界有哪太對勁?
》我頭跳,點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