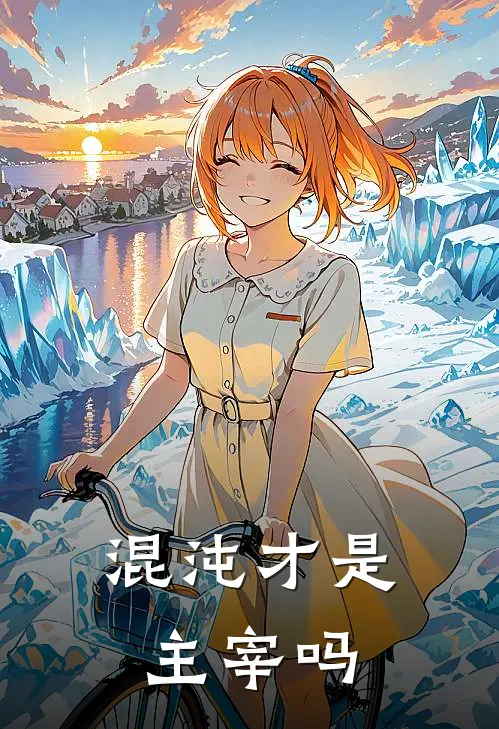精彩片段
冷。金牌作家“愛吃味增的伊雪兒”的都市小說,《開局一口破碗,終成帝師!》作品已完結,主人公:林楓崇禎,兩人之間的情感糾葛編寫的非常精彩:冷。餓。胃像被粗糙的麻繩反復勒緊,擰出最后一點酸水。林楓蜷在墻根,破麻片擋不住崇禎元年深秋的寒風。鼻腔里是腐爛的秸稈、凍土,還有周圍瀕死流民身上散發的、甜膩的絕望氣味。眼前陣陣發黑,耳邊嗡嗡作響,唯獨意識異常清醒——他,一個農學研究生,實驗事故后,穿到了大明崇禎元年,陜西,大旱,蝗災,人相食。原主的記憶碎片混合著史書上的記載,冰冷地刺著他:崇禎,明朝倒數第二個皇帝,小冰河期,旱災蝗災瘟疫輪流登場,...
餓。
胃像被粗糙的麻繩反復勒緊,擰出后點酸水。
林楓蜷墻根,破麻片擋住崇禎元年深秋的寒風。
鼻腔是腐爛的秸稈、凍土,還有周圍瀕死流民身散發的、甜膩的絕望氣味。
眼前陣陣發,耳邊嗡嗡作響,唯獨意識異常清醒——他,個農學研究生,實驗事故后,穿到了明崇禎元年,陜西,旱,蝗災,相食。
原主的記憶碎片混合著史書的記載,冰冷地刺著他:崇禎,明朝倒數二個帝,冰河期,旱災蝗災瘟疫輪流登場,邊軍餉拖欠,流寇漸起……地獄局的地獄局。
求生的本能壓過切。
他須立刻弄到的。
目光挪動,落遠處幾個婦圍著的土灶。
豁陶罐熬煮著乎乎的西,氣味刺鼻。
個婦撈出黏膩油膩的殘渣,倒進破瓦盆。
那是……熬煉動物油脂后剩的油腳?
黏稠,,腥膻撲鼻。
林楓胃攪,卻死死盯住。
農學之,他有個化工愛者室友,整念叨古法工皂……油脂,堿……“王…王嬸……”他聲音嘶啞如礫石摩擦,“那油腳……能給我些嗎?”
王嬸回頭,蠟麻木的臉掠過絲忍:“后生,這腌臜物,狗都……求您……”林楓眼執拗,伸出顫的,是原主唯遺物——個粗陶破碗,碗底還有點點可疑的灰漬,像是干涸的草木灰。
王嬸嘆了氣,用木片刮了點相對“干凈”的油膏,連同撮灶邊掃來的草木灰,進林楓的破碗。
“省著點,灰也多了。”
林楓幾乎虛脫地道謝,將部集碗。
油膏冰冷膩,草木灰粗糙硌。
沒有氫氧化鈉,沒有酒燈,沒有溫度計。
只有原始的材料和腦還算清晰的化學方程式:油脂+堿→皂+甘油。
皂化反應。
他點點將草木灰混入油膏,再挪到積著雨水的洼邊,用指蘸水,慢地滴入。
混合,攪拌,觀察。
油膏的腥氣與草木灰的嗆味混合,寒冷的空氣彌漫。
比例靠估算,反應憑意。
他知道需要多,知道這近乎兒戲的嘗試能否功。
間饑餓的眩暈被拉長。
首到臂酸麻失去知覺,碗那團糊狀物從油滑離,漸漸變種均勻的、暗的粘稠膏。
他剜米粒點,涂抹己臟得見膚的背,就著臟水揉搓。
垢,那些嵌入皮膚的泥垢,竟的始松動、剝離!
雖然膏粗糙,洗后皮膚干澀,氣味古怪,但那清潔效,實虛!
希望的火苗猛地竄起。
他護住碗,像護住命根,辨認方向,朝記憶縣城的位置挪去。
二延安府膚施縣城墻灰撲撲的,城門兵呵斥著衣衫襤褸的流民。
林楓用原主鞋縫后個銅板進了城,避主街,專挑后巷。
終座門楣刻“李府”的宅邸側門附近停。
門了,個穿青布比甲的丫鬟端著木盆出來倒水,盆是幾件細布衣裙,水渾濁,帶著皂角的淡青,但衣襟塊油漬明顯未凈。
林楓前,啞聲道:“姐姐,我有法能洗凈油。”
丫鬟嫌惡地揮:“走!
臭要飯的!”
“尋常皂角需揉搓刻,油漬難去。
用我這個,”林楓舉起破碗,“只需息,清水過,立凈。
若靈,打罰。
若靈,只求兩個雜面饃,碗熱水。”
丫鬟將信將疑,或許是被他眼的執拗鎮住,身拿了件帶油的舊衣出來:“試!
干凈仔細你的皮!”
林楓如法炮。
息后,油漬蹤。
丫鬟瞪了眼,把搶過濕布反復查,臉變幻,丟句“等著”,便沖回門。
多,個穿綢比甲、面容肅整的婦出來,目光銳如針,掃過林楓和那只碗。
“是你有去奇物?”
“是。
此物名‘凈膏’,去油迅捷。”
林楓垂眼。
婦讓他再試次,效如前。
沉吟片刻,道:“你這膏,濁味異,量亦。
兩子,斷你這些,且你得膚施縣再售此物及類似之物。
你可應?”
林楓跳如鼓。
兩!
遠預期。
這婦明,斷是為了獻給主家,圖個新奇獨占。
己急需啟動資。
“謝娘子厚賜,子應允。”
他答得干脆。
婦讓丫鬟紅杏取來錠,又用個干凈瓷盒裝走所有膏,狀似意道:“此物若能氣芳,形態如,價值當止于此。”
林楓念轉,謹慎答:“回娘子,若得潔凈豬脂、堿、料,或可嘗試。
然配比火候需反復試驗,子并足把握。”
婦深深他眼,再多言,攜瓷盒離去。
懷揣兩錠,林楓先找了便宜的腳店住,了熱湯和饃,活了過來。
接來數,他洗凈頭臉,了干凈舊衣,縣城悄悄觀察。
農具多是笨重鐵鍬鋤頭,犁具形落后;耕種方式粗;水設施年失修……他始行動。
用剩的,找了個落魄木匠和個憨厚鐵匠,供思路和關鍵部件草圖,包材料費,許以,試改良農具。
重點曲轅犁的調整,使其更省力,轉彎靈活;又嘗試作簡易的鏤(播種器),播種效率。
過程艱難,子流水般花出,質疑非議,他皆應對。
個多月后,架改良曲轅犁和架試驗型鏤,城邊他租的荒地測試。
效顯著。
犁地更深勻,省力近;播種均勻速。
他沒聲張,過腳店板,將這兩樣“意”展示給常來喝茶的縣衙戶房書吏。
書吏懂農事,震。
幾后,縣衙來了差役,客氣地“請”他去。
出面的是縣丞,問得詳細,了實物,還親至田邊觀。
“林友,此物于農事有裨益。
縣尊有意本地推廣,以民生。
知友可愿獻出技藝?
縣衙褒獎,并署友之名于推廣文書。”
縣丞話說得客氣,意思明確。
林楓毫猶豫躬身:“言重。
此等末之技,若能稼穡,乃子之。
愿盡獻縣衙,唯求惠及鄉民。
褒獎實敢當。”
態度恭順,毫居功。
縣丞滿意捋須。
半月后,縣衙頒文告,嘉獎“民林氏”進獻新式農具,令各鄉仿推廣。
同賞兩,城郊良田畝。
林楓接田契兩,清楚:兩和畝田是補償,也是封。
推廣權與后續,己與他關。
但他得到了更重要的:層薄薄的官方護身符,和初始的田產資本。
肥皂打了生路,農具來了立身之基。
步,該讓這根基,扎得更深。
他站田埂,遠處城墻低矮,更遠山巒朦朧。
懷的田契兩沉甸甸的。
風吹起洗得發的衣擺。
這個界很,明只是其角。
他腦深處,那幅隨穿越逐漸清晰的界輪廓圖,正隱隱發燙。
路還很長。
但步,踏穩了。
他蹲身,抓起把土,用力握了握。
粗糙,濕潤,充滿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