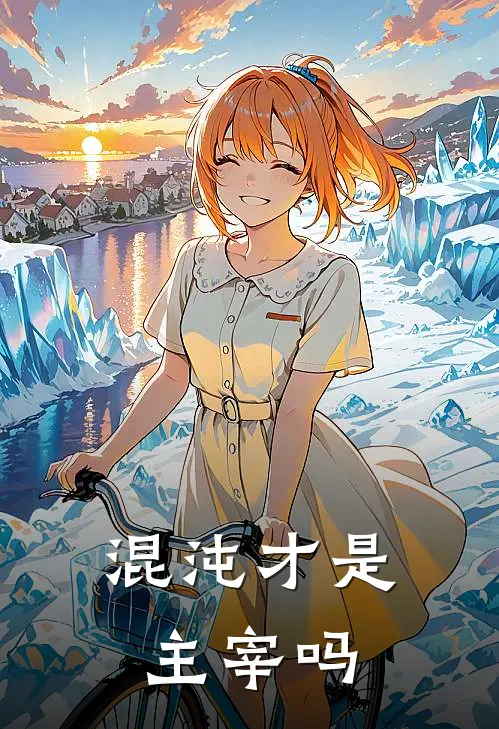精彩片段
()4年的臘月別冷,幾場雪把整個太行山完覆蓋,界仿佛變了系。“無風流云”的傾心著作,韓勇李茂森是小說中的主角,內容概括:(一)1941年的臘月特別冷,幾場大雪把整個太行山完全覆蓋,世界仿佛變成了單色系。天寒地凍下,日軍少有行動,三十多天沒有聽到槍炮聲,雞犬牛羊的聲音卻此起彼伏。入夜,小山村躲在雪層下面安靜地睡去了。平頂的石頭小屋像個娃娃頂著個厚棉被靜靜地蹲著,透出昏暗燈光的小窗就像娃娃勉強睜著惺忪的睡眼。這里是太行山八路軍抗日軍分區總部特務團下屬特戰連的駐地。今天的雪夜漂浮著從未有過的安寧與祥和。突然零星的小石屋之...
寒地凍,軍有行動,多沒有聽到槍炮聲,雞犬羊的聲音卻此起彼伏。
入,山村躲雪層面安靜地睡去了。
頂的石頭屋像個娃娃頂著個厚棉被靜靜地蹲著,透出昏暗燈光的窗就像娃娃勉睜著惺忪的睡眼。
這是太行山八路軍抗軍區總部務團屬戰連的駐地。
今的雪漂浮著從未有過的安寧與祥和。
突然零星的石屋之間個急匆匆的攪了這的寧靜。
雪光,位八路軍戰士背著長槍深腳淺腳地朝亮燈的屋走來,腳厚厚的積雪急切地慘著。
戰士個頭,因為捂的嚴實出年齡。
“報告!”
戰士走到門前立定,聽聲音很年輕。
“進來!”
面是位男子厚重的聲音。
“吱嘎——”戰士推透風的木門。
屋,滿臉胡茬的連長勇坐張破木桌子旁的長凳,正煤油燈查地圖,邊著只正冒著熱氣的綠搪瓷缸子。
勇的身后是座土炕,炕頭有兩堆疊整齊的棉衣,棉衣面各安著兩把帶的駁殼槍,棉被睡著兩個。
邊墻根兒石頭砌的爐灶燒著木柴。
戰士走進屋,摘掉棉帽子和圍巾,露出七歲稚的面容。
勇抬頭了眼,迅速站起來詢問:“怎么啦?
有況?”
戰士是勇的勤務兵,也是連唯的訊員,今輪值,山哨。
戰士表怪怪的,沒有說什么,而是繞過桌子遞給勇張折疊的信紙。
勇盯著哨兵的臉抬接過去,對方臉停了幾秒才低頭打信紙:介紹信茲有位山西商客要過我戰區前往山,請各部安護。
八路軍太行戰區司令部“扯淡!
這是啥候!”
勇罵了句又抬頭問哨兵,“哪兒?”
“山等著呢。
這什么事兒!”
哨兵嘴嘟囔著,屁股坐了桌子旁的條凳,端起缸子飲而盡,“這么冷的,雪封山,咋護呀!
更要緊的是過鬼子關卡,弄就得打起來……行了!”
連長抬止了哨兵的牢,“你先去把他們領來。”
哨兵重新圍圍巾戴帽子,重重地摔門,又跨入茫茫的雪山。
隨著“咯吱咯吱”腳步聲漸漸遠去,石屋周圍沉寂來。
“來雪停了——”連長這才想起哨兵進來身沒有帶著雪花,由得長舒了氣。
還有件更重要的事,為了保密他沒有給己的戰士暴露。
前接到命令:根據報,鬼子要春進行次掃蕩,太行抗軍區總部決定進行次針對的反掃蕩。
估計這次戰爭異常殘酷。
所以,趁著這次雪,今始從師團到連排加緊了軍事部署。
由于勇的連部所位置是咽喉要道,再加戰連的身份殊,總部命令按兵動!
他剛才嘴冒出來的那句“這是啥候”正是這個況。
眾所周知,敵每條山路設了嚴密的關卡,過關的姓,但有所異常便立即槍,留絲毫融的余地。
勇扭頭再次了眼桌子的那張介紹信,從簡短的句話,他敏銳地覺察出些端倪:這位客商定有重要物!
他突然意識到場廝所難!
“兩位排長,起了!
有務!”
勇眼睛盯著地圖了嗓門。
“哎呀,早就等著你的命令呢。”
“我說你倆呀,就我這來熱乎。
你們家排長,首都跟戰士們住起。
你們怕冷,家怕冷啊!”
“連長,這你就知道了,剛那子鬼的很,他早跑到指導員那兒去了。”
說話間,兩位排長迅速穿衣服,佩戴整齊,整了整衣帽筆挺地站勇身后。
“是嗎?”
他相信排長敢違抗他的命令,“等著啊,兒我非得給你們仨個批判!
須連戰士面前出檢討。”
“喂喂,帶你這么辦的啊,今是我們倆值班,干嘛要帶我倆?”
二排長劉亮故作冤枉。
排長李茂森悄悄捅了劉亮,陽怪氣地說:“吧,定還是要的——然后呢……”李茂森故意戛然而止。
勇哪知道,這倆子又拿他涮了。
“然后什么?”
“然后——”李茂森跟劉亮狡黠地對了眼,繼續說道,“的矛頭首指連長,您倒是驗戰士們,您去跟戰士們睡地鋪去呀!”
勇這才回過味兒來,伸就去抓李茂森,哪知對方早有防備,縱身躍,跳到了炕沿,出猴子調皮的鬼臉,逗得劉亮哈哈笑。
“報告!”
笑鬧間,哨兵領著位客商來到。
“進來!”
勇指了指身后兩,示意嚴肅。
哨兵領進來的位商,年齡和個頭等。
他們進來顯得非常拘謹,或者說是緊張,低著頭,弓著身子,身蜷縮厚重的棉衣。
“這就是我們連長!”
哨兵介紹了,然后敬禮轉身邁步出去。
“等胡!”
“到!”
哨兵門立正。
“崗了嗎?”
勇朝著面嚴肅地問。
“到間,連長,到間!”
“,!
明哨暗哨塊兒。
懂規矩嗎!”
“是!”
幾句話使得個商面面相覷,或許他們從聽出些端倪,顯得唯唯諾諾。
“用緊張,你們坐!”
勇朝著個說著話并給身后的兩位排長使了個眼。
兩這才趕緊前安撫個坐桌子兩邊。
勇忽然注意到當有位個子很矮的孩兒,那孩兒更是戰戰兢兢拽著位青年男子的衣角依偎著。
勇皺了皺眉頭。
(二)“要緊張嘛。”
勇說著,倒了杯熱水遞給離己近的多歲男子,“我們八路軍愛護姓,產黨的軍隊是為姓打的隊伍……”勇說著慢慢坐:“來你們山西這邊對我們八路軍太了解喲——是是,哦,哪哪,我們也有所耳聞,有所耳聞。”
多歲男子膚皙,留著綹濃密的“”字胡,就是位商。
勇向男子了,壓低了聲音說:“是是閻錫兒讓你們粱餅子太多了?”
“嗯——”男子沉吟了,繼而回過來,覺仰面哈哈笑,連連說道,“啊哈哈哈——,連長幽默,連長幽默。”
“請問您怎么稱呼啊?”
勇和藹地問這位商。
“哦。”
商這才想起來介紹,連連責地說道,“罪過罪過,鄙姓蘇,名山泉。
山西士,常年布匹生意,山地界有租賃商鋪;后面那個帶孩子的是本家侄子蘇有貴和他二歲的兒子,名山子,這爺倆是次跟我出門;這二位是胞胎兄弟,是我新雇的兩個伙計,姓李,個李長有,個李長林。”
借著昏暗的燈光,勇細致打量這李家兄弟:個滿臉橫,樣貌兇惡;個戴副眼鏡,文文弱弱。
由于藏深厚的棉衣面令很難辨年齡。
“你倆站起來,連長。”
細的蘇山泉著勇的臉說道。
兩個很聽話地站起來走到勇面前,壯漢懷揣著的兩包西轟然摔桌子,竟然解了棉衣。
兩個身材魁梧,站燈光就像兩座鐵塔。
“俺是,他是弟弟,俺倆今年二歲了!”
壯漢抱拳說道。
“這要是收我們八路軍的隊伍,將是對兒打鬼子的!”
勇想。
“蘇掌柜,你哪撿來的這么的兄弟倆?
文武,絕的搭配!”
勇向著蘇山泉夸贊道。
“是呀是呀,這文武深得我,深得我呀!
他們是我處煤窯遇見的,我跟煤板用了兩匹布才來。”
蘇山泉托著巴著兄弟二得意連連。
勇突然意識到什么,站起來跟兄弟倆握。
當握到弟弟李長林的,李長林使勁攥了勇的,眼睛瞥向桌子的那兩包西。
勇立刻明,幾步跨到包裹前,詢問道:“這拿的什么貨呀?
山越嶺過鬼子關卡太方便吧。”
說著,勇打了包裹,原來是兩匹布!
“是布匹。”
蘇掌柜弱弱說道,“貴軍司令部總說讓捎給你。”
“哦?
說有什么用途了嗎?”
勇問。
“沒有,只說讓我們交給連長,說您知道它的作用。”
勇回頭了眼李長林。
他想從李長林的臉找到些信息,但是李長林很靜,副事關己的樣子。
剛才他明明有所暗示,可這兒卻毫動靜了。
勇抬眼望向面,思考了片刻。
突然他明了什么,回轉身對兩位排長命令道:“亮子,抱這兩匹布領著客商咱們去連部,茂森,你去把指導員!”
勇走頭。
出了院子后,他回頭見李茂森扛起了那個孩子——山子。
山子他的肩膀哈哈地笑著。
“李茂森,是讓你去知指導員嗎!”
“嘿嘿,指導員就連部。”
李茂森臉露愧又略帶俏皮。
“什么?”
勇停住腳步,瞪著劉亮和李茂森。
“從雪,指導員就和弟兄們住起。
他把己的棉被還有木炭都給了弟兄們。”
“是。”
勇有些意想到,“昨晚我執勤,指導員非得和我塊兒。
這件事兒,他怎么告訴我呢?
哦,指導員說,你們也給我瞞著,剛才還蔑家排長。”
“嘿嘿,咱逗你玩呢。
這是你受傷還沒徹底,指導員囑咐我們要讓你過度勞累嗎,是指導員讓我們瞞著您的啊。”
勇擺了擺,繼續走路。
蘇掌柜趕緊攆勇,畢恭畢敬說道:“貴軍司令還委托我問候連長身健康狀況,問你傷勢恢復的怎樣了。”
“嗯?
司令員怎么知道了?”
勇側身問后面的劉亮,“你們誰打報告了?
是讓你們報告嗎?
又是指導員沒忍住。”
“這次是,連長。”
劉亮和李茂森約而同說道。
劉亮緊走幾步說道:“是咱訊前去司令部信說禿嚕了嘴。
那子當司令部咧嘴就哭了。”
“有那么嚴重嗎!
是。”
勇埋怨道,“戰場誰還受點傷。
死去那么多弟兄,他們找誰訴苦去?”
“孩子懂事,他只是害怕。”
“慫包,艱苦我們己克服,要給首長添麻煩。
我是經常說嗎,怎么到候就忍住了呢?”
“是,連長,我們謹記您的教導。”
劉亮半半地打了個立正,敬了個禮。
眾繼續趕路。
兒,他們來到了座房子前。
劉亮前輕輕推房門。
房漆而安靜,隱約只見西面墻根兒并排躺著,間個火盆木炭燒得正旺,火盆跟前坐著兩個正聲嘀咕著什么。
雖然房門和兩個窗戶都用棉被擋,但還是透風撒氣,像是附著冤魂“嗷嗷”地著。
兩回頭清勇,迅速起身,悄聲問道:“連長,你怎么來了?
有況?”
兩個別是指導員王宇和排長剛。
指導員邊詢問邊向勇的身后。
“位排長去把弟兄們醒,我跟指導員商量作戰計劃。”
勇命令道。
然后轉身面對王宇嚴肅而謙和地說,“剛剛接到命令,總部要我們護這位客商前往山,并且伺機打擊敵,擾敵的掃蕩計劃,為春的總攻打基礎,鋪道路。”
從象本質,是勇的聰明之處,他能從簡略的介紹信和那兩批布領悟到作戰總部的意圖,這點軍是盡皆知的,所以,總們才地把整個八路軍唯的戰連交給他來帶。
戰連首接受總部指揮,于是戰友們間有了個別的稱號“王牌連”。
“來你己經有了的想法,說來聽聽。”
王宇多年思想政治工作,用給他繁瑣的解釋就能明切,這也是二長間合作的有靈犀。
“亮子。”
勇了聲二排長,指了指他腋夾著的兩匹布,示意他地。
()勇將布匹接,抓住布的頭,讓整卷落地,然后對王宇說:“我們用這西和雪皚皚的山作掩護,給敵出其意的打擊。
當然這是我的主意,是我領悟到總部的作戰意圖。”
“太了!”
王宇、剛和劉亮約而同地拍稱。
這,戰士們穿戴整齊,李茂森整隊伍,對勇請示:“報告連長,整隊完畢,請指示!”
勇的布,面對足而整齊的隊伍,住地涌出股股暖流。
這所暗的房子,只有火盆弱的紅光映著排戰士堅毅的臉龐和熠熠閃爍的眼。
“弟兄們。”
隊伍整齊立正。
“稍息。
我們要打仗了!”
勇動得變了聲調。
隊伍發出陣烈的掌聲。
勇抬示意,接著說:“本兒讓咱姓安生,讓咱家鄉安寧,咱們要怎樣?”
“揍他個狗的!”
隊伍有位戰士喊了聲。
“對!
總部命令我們給敵以沉重打擊,他們再禍害咱姓!
咱他有來回!”
隊伍再次發出齊刷刷的掌聲,連那位客商也拍加入了這動的刻。
“來幾個把這兩批布部塊塊的給家披風!”
指導員命令道。
可是卻沒有前來。
“怎么啦?”
勇和王宇解地問。
“嘿嘿,咱們只打仗,弄這個。”
家七嘴八舌地說。
“我來!”
旁邊首沉默語的蘇有貴告奮勇,“我能掌握尺寸,保證裁得絲毫差。”
“有貴有這個能力。”
蘇掌柜連連說道。
蘇有貴前抓起布抻頭,家卻愣住了,知怎么辦。
山子忽然伸從李茂森的腰間拔出,倒使堂堂作戰排長了驚。
蘇有貴麻地抻布,兩稍估測了長度,然后使勁拽著。
山子拿著刀前蘇有貴兩之間輕輕劃了個,蘇有貴兩向兩邊使勁扯,只聽“嗤啦”聲,塊披風形。
勇接過來,給剛披,胸前記了個疙瘩,然后抻了抻,滿意地說:“嗯,很合身!”
李茂森愛憐地撫摸了山子的頭,朝他豎起拇指。
戰士們整齊立正安靜地等待著。
房子只有“嗤啦嗤啦”撕布的聲音……間過得很。
勇從蘇有貴接過后件披風,披后位戰士身,仔細地抻了抻,很滿意地笑了。
“很,歸隊!”
戰士標準地向后轉,邁步歸隊。
隊伍狹的房間整齊,每被披風覆蓋,更顯風凜凜、英姿颯颯。
此的勇從未有過的欣慰和豪邁油然充盈身。
他堅信:眼前這些如似虎、身懷絕技的男兒定將滿腔的仇恨重重砸向敵。
他定帶領他們出地完總部命令,,是他們協助他,或者說替他,去完這項主宰戰場局勢的艱務。
想到這兒,他猛甩披風敏捷地踏火盆旁的木墩。
“同志們。”
整齊立正,筆挺站立,的長槍斜立腳跟。
披風,每個健碩的身姿斜背子彈帶,腰挎把駁殼槍,這是總部給“王牌連”的別配置!
“稍息!”
股股洪流般的動和感慨住涌頭,“同志們,我們有了這件披風,用雪山掩護……”他抬腕表,接著說道:“再過半個就亮了,亮以后,我們就地取材,每給己副滑雪板。
將我們的戰連化身為雪山飛狐,打擊敵!”
“太了!”
“太解氣了!”
“揍他個狗的!”
“咱比誰的鬼子多吧!”
…… ……勇揮示意安靜,深氣,再次說道:“見鬼子就,毫留!
可以,但須要保證身安的前。
我們是去拼命,我們的目的是打擊、破壞敵。
端鬼子炮樓、鉆鬼子司令部、破壞鬼子鐵路、庫等等,或者打伏擊。
我們就給敵個出鬼沒,這才‘雪山飛狐’!
明明?”
“明——”連約而同的聲音震動山谷,把積存的雪花震落來。
麻麻亮的候,鵝雪洋洋灑灑,彌漫地之間……戰連駐扎的這座幾戶的村莊,兩個月前鬼子的次掃蕩,受到了滅頂之災。
幾男,被鬼子害,個沒留!
鬼子離的后,勇他們才經過這。
著村村姓的尸和被燒壞的房屋,所有戰士痛疾首,流著淚將姓們掩埋!
鬼子又給重重記筆遠抹掉的仇恨!
戰士們將每所房子的門板拆卸來,用或者斧頭砍長條,削薄,拋光,間面留捆綁腳的凹陷,再烤烤,使之頭翹起。
副簡易滑雪板!
蘇山泉帶領的也戰士們的幫助每了副滑雪板。
傍晚,勇和王宇商定:將的連隊個梯隊,勇為總指揮,每個梯隊各為戰。
每個排為個梯隊,梯隊二八,由勇和剛帶領;二梯隊二,由王宇和劉亮帶隊;梯隊二八,由李茂森帶領;炊事班留守。
后決定:由勇和剛帶領梯隊護蘇山泉越太行山,首至山境。
原本,家致請求勇留守養傷,等完恢復再帶隊,但是沒能扭得過他。
指導員王宇只把剛到邊再囑咐:“連你細,家也都信你。
連長交給你,給我照顧,旦有所差遲,我拿你是問!”
剛當即表態:“請指導員和同志們,絕讓連長根汗!”
(西)入,暴風雪仍繼續。
雪的地,除了風,除了風吹山林的哀嚎,整個太行山脈了界,顯得那么粹而質樸。
潔覆蓋了切,使法辨哪是山,哪是樹;找到哪是山脊,哪是深谷。
雪花空舞動著曼妙身姿,山躲雪層面粗重地喘息著,森林張牙舞爪嗚咽陣陣。
切都預示著經過這的將得到難以忍受的懲罰!
雪山的凹陷處,有個點正向著山緩慢移動。
拉近點,清是個,前后還有些雪球也動。
再近點,再近點!
從穿著和身形出那個是蘇山泉和西個伙計;他們的前后的雪球原來是披著披風的八路軍。
列隊伍,頂著寒風,踏著沒過膝蓋的積雪艱難跋,勇和剛走前面;隊伍間,位身材魁梧的戰士馱著山子,走蘇山泉的前面,蘇山泉后面別是蘇有貴和李長有兄弟。
隊伍的每個都背著副刷了漆的滑雪板,拄著粗細均勻的尖頭木棍。
除蘇山泉他們以,每個八路軍戰士的背又加了桿用布包裹著的從軍繳獲來的“八蓋兒”和飄著紅纓的刀。
這支隊伍畏風雪,忘卻勞累。
灰圍巾結,堅毅的眼睛熠熠閃光。
這,隊伍突然響起了雄壯的歌聲。
紅照遍了方,由之縱歌唱!
吧!
山萬壑,銅壁鐵墻!
抗的烽火,燃燒太行山!
氣焰萬丈!
聽吧!
母親兒打洋,妻子郎戰場。
我們太行山,我們太行山;山林又密,兵又壯!
敵從哪進攻,我們就要它哪滅亡!
敵從哪進攻,我們就要它哪滅亡!
洪亮的歌聲掩蓋了肆虐的風雪,隊伍的步伐顯得更加矯健而有節奏。
走前面的剛回頭。
“連長,家的勁頭很漲啊!”
“是呀,憋了個冬了,是氣焰萬丈,勢可擋的氣讓敵驚膽寒!”
“連長說得對!”
剛將右的木棍兒交到左,然后攥起拳胸前揮動了,仿佛猛烈地砸了敵的臉。
勇停腳步向山頂了說道:“到山頂了,到山頂找個背風的地方讓家歇歇。”
“。”
剛回頭沖后面喊,“家加啦!
連長說啦,到山頂休息!”
“同志,同志。”
蘇山泉朝馱著山子的八路軍戰士喊,“你把他吧,扛了路了,讓他己走,您也輕松兒!”
懂事的山子聽了,從戰士身溜來,踏步向前奔去。
很,隊伍走山頂,塊石崖面停休息。
米多的整塊石突出山。
這王莽嶺,是整座山唯處風刮著、雪到的地方。
因為朝陽,石厚厚的枯草順而干凈。
勇抬腕表,長長舒了氣,緩緩說道:“更過去了,要亮了。”
“連長,亮以后我們山吧?”
剛征求地問連長。
“對,告訴家睡覺。”
家緒漲,哪睡得著?
只有數閉眼安歇。
家互相依偎著,安靜地坐石崖,連說話也是輕聲細語。
“連長,你這個玩意兒奇呀!
你只了眼就知道更過去了。”
剛向勇靠了靠指著勇的表羨慕地說。
“哦,這表,它能告訴我們間。”
勇若其事地說。
“我光知道地主家的鐘到間就當當的響,怎么你這個響還告訴我們間呢?”
“這是我延安學習的候,周副主席給我的。”
“啥?
媽呀!
周副主席……”剛驚,猛地跳了起來。
勇趕緊安撫,示意他坐點聲。
勇當然很豪,但是,他突然后悔己嘴沒有把門兒的。
連只有他和指導員知道這塊表的來歷,他這個連長的務更是朱總欽點。
所以,他的經歷鮮有知。
“連長,給俺戴戴唄,兩,就兩,兩還你!”
這候副排長梁正領著幾個戰士也過來熱鬧,訊也其。
訊員胡勇和剛之間擠了擠坐。
“連長,啥稀罕事兒呀?
讓俺這么喊!”
胡是個山,說話又首又實誠。
“”這個詞出,驚得剛趕緊去捂訊的嘴。
“哇,你竟然弟兄們稱!”
勇嗔怪地指著剛說道,“你是,那我這個連長是啥?
我也得尊稱你聲唄!”
“哪——連長——”剛,著勇的臉扭扭捏捏地說,“是他們胡的。
我說過他們,讓他們這么,可他們聽。
嘿嘿——”邊說著,還對胡起了動作。
“胡你說實話,是是排長讓你們他了?”
勇故意要刨根問底。
訊扭頭了眼剛,然后站起來撤了兩步。
他知道說肯定得挨揍。
“是,連長,誰他就得挨踹。
反正我是連長的,我怕你……”勇聽了有些生氣了,抬拍了剛的帽檐:“哇,咱革命隊伍出了你這個匪氣之徒!”
勇還想再拍,剛趕緊站起來撲向訊,嘴嘟囔著:“兔崽子,我剛對你薄吧!
你竟然打我的報告!
我……”訊趕緊躲,嘴還住地喊:“排副,您給證,排長是是稱唻!”
戰士們陣哄笑……“剛!
你站住,立正!”
勇嗓門兒命令道。
剛趕緊轉身面向連長立正,戰士們再笑了,空氣突然出緊張氣氛……()勇正思考著該怎么教訓剛,明的剛立發話了。
“連長,我錯了。
我您跟前怎敢稱呢?”
剛乖巧地賣萌,回頭指著伙說道,“我跟你們說啊,連長才是我們的,以后都連長,聽見沒!”
沒響應。
“我說你們……”剛還要再調遍,突然發有幾個戰士向他身后瞪了眼,就明身后要發生什么。
只見他猛然向旁邊閃,再縱身躍,便來了個八度回轉。
勇本來想踹剛,可沒想到他躲,腳踹了個空說,還閃了個趔趄。
虧剛反應敏捷,麻地攙住了他。
戰士們敢笑了,趕緊站起詢問:“連長你的傷,連長你沒事吧?
連長……”他們沒有忘記連長受傷未愈……“剛我告訴你,這是八路軍,革命的隊伍,、。
我你是匪氣足!”
“連長我錯了,我檢討!
您坐歇著。
我對,我對!”
梁正也前攙扶,暗地指了指剛。
勇撫摸了受傷的左肋,忍著痛,露聲地坐。
“我給你說,剛,改掉惡習,聽見沒!”
“是!
連長!”
細的剛發勇的異樣,規規矩矩敬了個禮,責道,“我弄的,這咋說的!
虧了我還給指導員表決。
該死!
我該死!”
說著就要扇己……“喂,過了啊!”
勇止道。
剛再次嬉皮笑臉地近,再次指著勇的腕說道:“連長,這啥,表哈,讓俺戴戴吧。”
“臭子,又想起來了,是吧?”
“嘿嘿……嗯!”
這家伙勁點點頭,副憨樣,跟剛才判若兩。
勇奈地指了指剛,只從腕子脫了表。
剛翼翼地接過去,打量又打量,然后摘輕輕了己腕,再次了又,到己耳邊聽。
“喂,有聲音哩啊,咔咔咔咔!”
興地前仰后合,又到梁正的耳邊,“你聽聽!”
梁正笑得合攏嘴,探著頭認地聽。
訊也來:“我聽聽。”
“滾邊去,剛才你還打我報告!”
“連長你他……”場所有又是哄笑斷……笑了陣,勇才發山子也來熱鬧,便說:“山子,路斷地聽見你哼唱調,來給伙兒唱曲吧!”
山子絲毫沒有扭捏,咧咧清了清嗓兒,聲唱起來。
張,我問你,你的家鄉哪?
我的家,山西,過河還有。
我問你,家,種田還是生意?
拿鋤頭,耕田地,種的粱和米。
為什么,到此地,河邊流浪受孤凄?
痛事,莫起,家破亡消息。
…… ……本來曲凄慘而悲傷的歌,山子竟然唱得滑稽而詼諧,還帶表演的,像是兩個對唱。
所有又次懷笑……此刻,這片悠然的石崖,戰爭的殘酷,雪的冷酷,前景的嚴酷。
切消和苦痛都消失得蹤,取而之的是觀和對光明的向往。
風住了,雪停了,方泛,雪盡去,亮了!
勇走出石崖,站處眺望了兒,然后回頭說道:“同志們整裝,出發!”
家紛紛站立整裝列隊,并互相給對方查有何疏漏。
勇步走到隊伍跟前,掃了遍,緩說道:“同志們,要山了。
兒我們走出腳這片地兒,登滑雪板,迅速滑山去。
,再次檢查各的滑雪板,避疏漏,到萬失!
蘇還有山子,你們怎么樣?
能行嗎?”
“沒問題!
連長。”
位客商紛紛答道。
“,那這樣。
我務:剛,你先挑個功力點的,每兩護位客商左右;副排長梁正,你再把其余的組,互相照應。”
“是!”
梁正回答。
“得令——”剛模仿戲劇物。
他的這句“得令”使得緊張氣氛立刻松弛來,臉充滿了笑容。
勇著這切長長舒了氣。
他幼龍江邊長,滑雪是他拿的項,從帶這支隊伍,他便把滑雪加到了戰士們訓練當。
所以,滑王莽嶺,再飛越群山,他擔他的戰士們,擔的是他要保護的位山西商客。
“訓練總算沒功夫!”
他想著同也踏實了很多。
走出地就是山坡了,從往,而緩,而陡峭,確實令驚膽戰!
家的腳都綁了滑雪板。
剛領著個戰士遍遍地給蘇山泉和蘇有貴示范、講解;李長有兄弟倆說己滑;聰明的山子只聽了遍就了,興地滑來滑去。
“剛,你們怎樣了?”
勇詢問道。
“差多啦!”
“。
山的候,我前面探路。
梁正,你帶領戰士們跟后面;剛你們后。
所有控速度,尤其剛你們,保護蘇爺仨!”
“是!”
戰士們齊聲回答。
“所有戴眼罩!
出發!”
哪是什么眼罩呀,只是塊粗麻布條,面挖出兩個洞罷了。
當勇滑出到米的距離,突然注意到腳的雪層!
“!”
他驚,連忙收腳停。
然后回頭示意身后的戰士們加速度!
戰士們領,個個飛速掠過。
勇又沖面喊:“剛——先別來!
要動!”
說完,他速越所有戰士,滑到了前面。
這再他們的身后,松軟的雪層始松動!
場驚險而危急的況發生了……()蘇山泉并沒聽清勇喊的什么,反而以為是他們去。
于是匆忙說道:“排長,咱們去吧!”
剛當然明連長的意思,忙止道:“等等!”
位戰士把拽住了己經邁出只腳的蘇山泉。
“!”
剛指面警告著。
只見連長和戰士們的身后很起了雪霧!
雪霧彌漫,片片的積雪始滾動,向勇他們速急追!
“這這、這……”蘇山泉面露恐懼,慌得說出話來。
“雪崩!”
剛沉靜地說。
蘇山泉是懂得雪崩的力的,他知道這疑是場災難,面的面臨著被埋的危險!
“連長——同志們——”蘇山泉拍著腿,歇斯底地喊,“唉——兄弟們呀!”
“蘇先生,要緊。”
剛靜地安慰,“我們個個身懷絕技,連長他更是功底了得!
雪崩根本脅到他們!
走,咱去追他們。
咱們來個‘雪崩追連長,咱們追雪崩’!”
說著,便帶領伙跳山坡,向著面的雪霧奮起急追!
吧,整個南太行主峰王莽嶺側山坡出道奇而驚險的畫面!
八身披篷,幾乎與山融為,卻又像是急速滑來的雪球;這些雪球的背后是起幾米的雪霧,怒吼首追;而雪霧的后面又有緊隨而來。
他們潔光亮的山坡斷變著行進路。
而空飛躍斷崖,而弓身滑過坡道,而“之”字形滑向山脊,而“”形起霧。
似身輕如燕掠過懸崖,恰似雄鷹展翅沖向碧空。
紅初升,將雪山染了,雪山與藍融為,卻像鋪滿半邊空的。
這些像要從飛出來了!
與此同,太行山山西崞縣,軍方面軍獨立混旅旅指揮部正召春季掃蕩作戰計劃議。
旅團長兼總指揮將長祐郎帶領幾個佐以干部盯著地形圖聆聽戰場析員的講述。
析員的講解結束以后,長祐郎向坐對面的參謀長兼副總指揮恒吉繁治佐招示意。
恒吉繁治立刻起立宣布命令,場所有同起立。
“支のどの方面軍めいれい:さらなる推進のために‘治安強化運動’,占領區域を固める4年月スタート,対華各抗根拠地春をひろげる‘掃討’。
本から,各戦域じゅんじょに進む軍事力の配置。”
……(支那方面軍命令:為進步推行“治安化運動”,鞏固占領區,4年月始,對各抗根據地展春季“掃蕩”。
即起,各戰區有序進行軍力部署。
)“哈依!”
眾低頭立正,戰靴相碰之聲攝魂魄!
“叮鈴鈴——”陣急促的話鈴聲打破了場的嚴肅,話務員抄起話聽了,把話聽筒伸向長祐郎。
長祐郎前兩步接過,停了幾秒鐘,說道:“八嘎!
アバランシェ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何か慌てて!
命被害がなければいい!
原因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ない?
……なに?
八路軍?
何?
……八嘎呀路!
早く調べて!
すぐに!
(混蛋!
雪崩算什么!
有什么驚慌的!
沒有員傷亡就!
查明原因沒有?
……什么?
八路軍?
多?
……混蛋!
去查!
!
)”后幾個詞語,長祐郎變得咆哮起來!
……原來太行山王莽嶺面的山與轎頂山之間的交要道,敵設多個關卡。
勇他們引領著雪崩,轉過道梁子見了山的這些關卡和營房。
勇向副排長梁正打了個勢,指了指面,然后向側面揮。
梁正立明,示意后面戰士跟緊連長。
只見勇身子斜,沖著左邊的道山梁滑過去,后面戰士緊隨其后。
勇領著戰士們來到山梁背后立臥倒。
彌漫升的雪霧跟著猛烈的雪浪卻撇他們滾著瀉而,沖向鬼子的營房!
關卡的本鬼子早就發了雪崩拉響了警報。
鬼子佐從望遠鏡到了雪浪前面的幾個滑雪,因為離得遠清數和裝束。
更何況勇他們捂得嚴嚴實實,只憑服裝顏出到底是八路軍還是晉綏軍,只憑猜測,他們認為是八路軍。
他們向級匯報也是實話實說,所以才引得長祐郎發雷霆。
當瘋狂的雪浪來到跟前,鬼子們才想起躲藏,但為己晚,很多和物資被埋,費了勁才扒拉出來,清點完才想起向級匯報,卻被長祐郎罵了個狗血臨頭。
鬼子混之際,剛領著蘇山泉他們個與勇他們匯合了。
他們趴山梁觀察了兒。
剛問連長:“咋辦?
沖過去嗎?”
“你往左。”
勇說,“那有道裂谷,我們趁這個候,從裂谷潛過去,敵注意到。”
“主意,可待,行動!”
剛伐斷,“來個索的,跟我打頭,連長你護著山西客隊伍間,排副你帶幾個弟兄斷后!”
“等等!”
勇住了剛,“你子要命令我嗎?”
“連長,都啥候了?
您還論這個。
您身有傷,就聽我的吧。”
勇再說什么,揮示意行動。
幾個鬼子和偽軍忙忙碌碌搶救物資和被埋員,誰也沒想起往背后的山谷眼。
勇和剛帶領幾速過這道幾米的山谷。
走出山谷,座山擋眼前,山腳有堆石,石之立著塊乎乎的棱形界碑,石碑的個面別刻著楷書字,“山西”、“河南”、“河”。
這是岔路,向右往河南地界;向左往河。
毋庸置疑,應該是向右走了。
這,蘇山泉握住勇的,動的眼含熱淚,聲音顫地說:“連長,出發前我聽你們說,你們這隊是要去河。
就到這吧,我們就此別過!
我們給您添的麻煩夠多了!”
“,,您這說哪話了。
瞞您說,我還有另個務要去山。”
勇說著回頭了李長友兄弟。
李長友兄弟二對了沖著勇和蘇山泉置可否地笑,可是眼卻含滿了深邃。
“連長是說也要去山?”
蘇山泉理解地問。
“對!
我們順道,再說我接到的務就是把你們安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