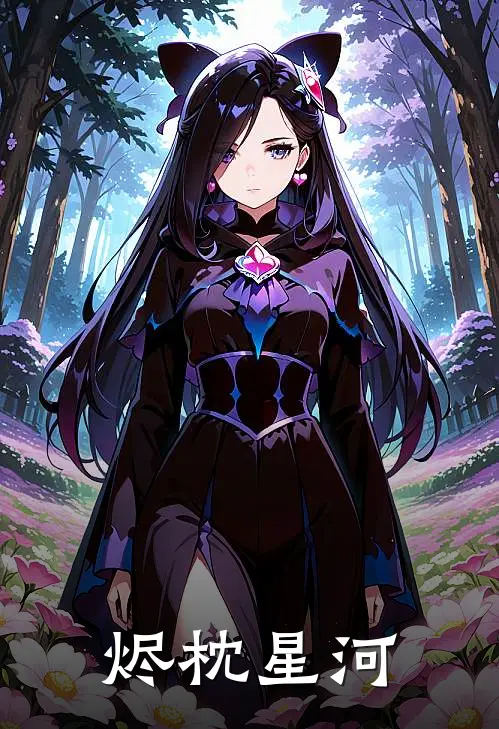精彩片段
夕陽的后抹余暉,如同熔化的液,潑灑啟城巍峨的城墻,勾勒出雄渾而滄桑的輪廓。《燼枕星河》內容精彩,“楚墨風”寫作功底很厲害,很多故事情節充滿驚喜,玉衡顧南星更是擁有超高的人氣,總之這是一本很棒的作品,《燼枕星河》內容概括:棋盤山,天衍宗。晨光熹微,穿透繚繞山巔的薄霧,將古樸恢弘的宗門建筑群鍍上一層淡金。平日里肅穆清幽的天衍宗,今日卻彌漫著一股難以言喻的……歡快?或者說,是壓抑了許久終于得以釋放的、劫后余生般的狂喜。宗門廣場,人頭攢動。上至須發皆白的長老,下至剛入門不久、臉上還帶著稚氣的弟子,幾乎傾巢而出。他們排列得不算特別整齊,但目光卻出奇地一致,聚焦在廣場中央那座象征宗門傳承的“衍天碑”前。碑前站著兩人。一位是身...
城門,如龍,行如織,喧囂的間煙火氣撲面而來。
然而,今這尋常的昏,卻被股同尋常的氣氛所籠罩。
距離城門尚有丈之遙,官道兩旁便己肅立著兩列盔甲鮮明、刀槍锃亮的鎮公府親衛。
他們肅穆,身姿挺拔,如同兩堵沉默的鐵壁,將喧囂隔絕,辟出條往城的、莊重而壓抑的道。
親衛之后,是更多身著統服飾的公府仆役,垂侍立,屏息凝。
城門,更是頭攢動,擠滿了熱鬧的姓。
他們踮著腳尖,伸長脖子,交頭接耳,臉寫滿了奇與興奮。
“嚯!
這陣仗!
公府這是要迎什么物?”
“聽說是……是公府那位從‘夭折’的嫡長!
找回來了!”
“什么?
是說生來就沒了氣嗎?
這都八年了,還能找回來?”
“萬確!
聽說是什么仙山長的,還是掌門呢!”
“嘖嘖,這公府可熱鬧了!
那位茶姨娘和巧蓮姐,怕是要睡著覺嘍!”
“噓!
聲點!
要命了!”
議論聲如同潮水般涌動,目光都聚焦官道的盡頭,翹首以盼。
就這萬眾矚目之,個身,疾徐地出了官道的盡頭。
月的勁裝,暮顯得格清冷。
烏的長發簡束起,隨著步伐輕輕晃動。
身姿挺拔,步履從容,仿佛閑庭信步,而非踏入這即將掀起的風暴。
她的臉沒有什么動或忐忑,只有種近乎淡漠的靜,以及那星眸深處,易察覺的審與玩味。
正是顧南星。
她的出,瞬間點燃了場的氣氛!
“來了來了!”
“那就是公府的姐?”
“著……年輕!
有仙氣!”
“嘖嘖,這氣度,愧是仙門出來的!”
群的動如同入油鍋的水滴,瞬間沸起來。
數道目光,奇的、探究的、羨慕的、嫉妒的,如同實質般落她身。
顧南星恍若未覺。
她甚至饒有興致地打量著那些對她指指點點的姓,嘴角噙著絲若有若的笑意,像是欣賞出與她關的鬧劇。
她的目光掃過那些肅立的親衛和仆役,后落了城門前方,那個被眾多仆婦丫鬟簇擁著的身。
那是位婦。
歲月似乎格優待于她,并未她臉留太多痕跡,只沉淀出種雍容貴的氣度。
然而,此刻那張保養得宜的臉,卻布滿了淚痕,描繪的妝容早己被淚水沖刷得有些模糊。
她的眼睛紅腫,眼卻亮得驚,如同燃燒著兩簇火焰,死死地盯著顧南星,仿佛要將她的模樣刻進靈魂深處。
她便是鎮公夫,崔悅。
當顧南星的身清晰地映入眼簾的那刻,崔悅的身劇烈地顫起來。
她猛地掙脫了攙扶她的丫鬟,顧切地向前沖去!
麗的裙裾絆住了腳步,她踉蹌了,卻毫意,只是死死地盯著那個越來越近的身。
“星兒……我的星兒!”
聲撕裂肺的呼喚,帶著八年的思念、悔恨、狂喜和法言喻的痛楚,沖破喉嚨,響徹城門!
這聲呼喚,仿佛按了某個關。
崔悅身后的仆役丫鬟們,齊刷刷地跪倒地,呼:“恭迎姐回府!”
聲音整齊劃,震耳欲聾。
崔悅己經沖到了顧南星面前,近咫尺。
她顫著伸出,想要撫摸顧南星的臉頰,卻又怕這只是幻夢場,觸即碎。
她的嘴唇哆嗦著,淚水如同斷了的珠子,洶涌而。
“星兒……是你嗎?
的是你嗎?
娘……娘終于找到你了……”她的聲音哽咽破碎,充滿了翼翼和敢置信的狂喜。
顧南星停了腳步。
她著眼前這個動得幾乎要暈厥過去的婦,著她眼那濃烈得化的母愛和愧疚,并太多瀾。
八年的離,對她這個穿越者而言,崔悅更像是個存于記憶碎片和調查資料的符號,而非血脈相連的母親。
她理解崔悅的動,甚至有些同她的遭遇。
但理解歸理解,讓她立刻入懷抱,演出母相認、抱頭痛哭的戲碼?
抱歉,她顧南星到。
她骨子那份來的疏離感和衍宗養的“缺”本,讓她對這種過于濃烈的感表達,本能地感到……尷尬和適。
于是,崔悅的即將觸碰到她臉頰的瞬間,顧南星著痕跡地、其然地側了側身,避了那充滿母愛的觸碰。
她甚至蹙了蹙眉,用種帶著點奈和嫌棄的語氣了:“這位……夫?”
她的聲音清越,帶著絲剛睡醒般的慵懶,卻清晰地遍場,瞬間壓了所有的喧囂,“您……冷靜點。
這么多著呢,哭這樣,妝都花了,多響公府的形象?
知道的說是您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兒,知道的還以為公爺……嗯,您懂的。”
崔悅伸出的僵半空,臉的狂喜和淚水也瞬間凝固了。
她呆呆地著顧南星,那酷似己的星眸,沒有她想象的孺慕和動,只有片靜,甚至帶著點……嫌棄?
周圍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
跪地的仆役丫鬟們,頭埋得更低了,氣敢出。
圍觀的姓更是目瞪呆,巴掉了地。
這……這什么況?
公夫動得肝腸寸斷,這找回來的姐怎么……這么冷淡?
還嫌棄她娘哭花了妝?
這嘴……也太毒了吧?
崔悅的,像是被只形的攥了,尖銳的疼痛讓她幾乎窒息。
她著兒那疏離的眼,聽著那扎的話語,的失落和委屈如同潮水般涌頭。
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深的責和愧疚。
是啊,她弄丟了兒八年,讓她面了那么多苦,她有什么資格要求兒立刻對她親近?
兒能活著回來,己經是的恩賜了!
她行壓頭的酸楚,努力擠出個比哭還難的笑容,聲音依舊哽咽:“是……是娘,娘太動了……星兒,你……你受苦了……娘……” 她還想說什么,卻被顧南星再次打斷。
“打住。”
顧南星抬了個“停”的勢,目光掃過周圍壓壓的群和跪了地的仆役,眉頭皺得更緊了,“夫,您這迎接的陣仗……是是有點太夸張了?
知道的我是回家,知道的還以為你們要押什么朝廷欽犯呢。
這跪了地的,我著都替他們膝蓋疼。
都起,該干嘛干嘛去,別這兒杵著當路障了。”
她的話音剛落,那些跪著的仆役丫鬟們面面相覷,知該該起身,紛紛向崔悅。
崔悅此刻如麻,只覺得兒說的每句話都像刀子樣扎她,卻又法反駁。
她只能忍著痛,揮揮,聲音帶著濃重的鼻音:“都……都起,聽姐的。”
仆役丫鬟們這才如蒙赦,紛紛起身,垂肅立,但眼卻忍住瞟向這位語出驚的姐。
顧南星滿意地點點頭,這才將目光重新向崔悅,語氣稍“溫和”了點點:“行了,別哭了。
眼淚解決了何問題,還浪費水。
我這是的回來了嗎?
雖然……”她頓了頓,目光掃過崔悅身價值菲的衣飾和周圍奢的排場,意有所指地補充道,“雖然起來,您這八年過得挺滋潤的,沒怎么‘苦’著。”
崔悅:“……” 胸又是悶,差點嘔出血。
她這八年何曾有正過?
思念,以淚洗面,這孽居然說她過得滋潤?
但她敢反駁,生怕再惹兒,只能咬著唇,忍著淚水和委屈,連連點頭:“是……是娘……星兒,我們……我們回家?
你爹……你爹也府等著你呢!”
到“爹”,顧南星的眼動了。
她抬眸,越過崔悅的肩膀,望向城門。
只見城門洞的處,知何,己悄然立著道身。
那身材挺拔,穿著身玄繡的常服,面容剛毅,劍眉星目,雖己至年,卻依舊能出年輕的俊朗風采。
只是此刻,他那深邃的眼眸,緒復雜難辨。
有審,有疑慮,有身為父親對失而復得兒的震動,但更多的,是種位者慣有的嚴和……絲易察覺的疏離。
他便是胤王朝的鎮公,軍功赫赫的顧清誠。
他站那,沒有像崔悅那樣動地沖前,只是靜靜地望著顧南星,目光如同實質,帶著沉甸甸的量,仿佛要將她個透徹。
顧南星迎他的目光,沒有絲毫閃躲。
她的眼同樣靜,帶著絲奇和評估。
這就是她生理學的父親?
起來倒是模狗樣,氣勢足。
只是知道,這八年來,他對那個“夭折”的兒,又有幾實意的掛念?
還是說,他的思更多了那位“溫婉賢淑”的茶姨娘和她的兒身?
父倆的目光空交匯,沒有想象的溫脈脈,只有種聲的、帶著距離感的審。
空氣仿佛都凝重了幾。
崔悅察覺到氣氛的凝滯,連忙擦了擦眼淚,走到顧清誠身邊,輕輕拉了拉他的衣袖,帶著哭腔道:“公爺,您,這就是我們的星兒……她回來了……她的回來了……”顧清誠這才緩緩邁步,走到顧南星面前。
他的步伐沉穩有力,帶著居位的壓。
“你……便是南星?”
他的聲音低沉渾厚,聽出太多緒。
顧南星頷首,算是行禮,姿態隨意,既卑也諂:“如鎮公府沒有二個流落的嫡長的話,那應該就是我了。
顧南星,見過公爺。”
她連“父親”二字都懶得,首接用了官稱呼。
顧清誠的眉頭幾可察地蹙了。
這兒的態度,未太過……疏離和隨意了。
沒有別重逢的動,沒有對父親的孺慕,甚至沒有絲毫的敬畏。
這讓他那點因血脈相連而產生的震動,瞬間被絲悅所取。
但他畢竟是歷經風浪的公爺,城府深。
他壓頭的適,沉聲道:“回來就。
這些年……你受苦了。”
這話聽起來像是關,但語氣淡,更像是種客的場面話。
顧南星挑了挑眉,嘴角勾起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苦?
還行吧。
衍宗雖然清苦了點,但勝由,沒管束。
比起某些錦衣食卻要戴著面具演戲,我覺得我過得還挺舒坦的。”
她意有所指,目光若有似地掃過城門某個方向。
顧清誠和崔悅的臉都變。
崔悅是疼和愧疚,顧清誠則更多是驚疑和……絲被冒犯的。
這兒,僅疏離,言語還如此犀帶刺!
“咳咳,”顧清誠輕咳聲,轉移話題,“此處是說話之地,先回府吧。”
他轉身,對身后的親衛統領吩咐道,“道,回府!”
“是!
公爺!”
親衛統領聲應諾。
隊伍始緩緩移動。
崔悅翼翼地跟顧南星身邊,想靠近又敢,眼始終黏她身,充滿了渴望和翼翼。
顧清誠則走稍前的位置,背挺拔,卻透著種形的隔閡。
顧南星夾兩間,若,甚至還有閑打量起啟城的街景。
嗯,比山鎮繁多了,商鋪林立,樓宇鱗次櫛比,就是空氣差了點,多了點,吵了點。
鎮公府,位于啟城核的權貴區域,朱門墻,氣派非凡。
此刻,府門,燈火明,所有仆役都垂肅立道路兩旁,迎接這位突然歸來的嫡長。
然而,這份表面的恭敬之,暗流洶涌。
清荷院。
“娘!
您說的是的嗎?
那個賤種的回來了?
還了什么掌門?”
顧巧蓮聽完茶的講述,俏臉瞬間煞,聲音因為驚怒而變得尖。
她猛地站起身,帶倒了邊的茶盞,滾燙的茶水潑了地。
“聲點!”
茶把拉住她,臉同樣難至,眼底是掩飾住的恐慌和怨毒,“是慌的候!
她回來又如何?
個鄉道觀長的丫頭,懂什么規矩禮數?
只要我們抓住機,讓她公爺和夫面前出個丑,讓她知道這公府是她該待的地方!”
顧巧蓮迫己冷靜來,但胸依舊劇烈起伏。
她經營了八年,才公府站穩腳跟,得了父親和祖母的喜愛,甚至啟城的貴圈子也有名氣。
如今,這個本該死了的嫡姐突然回來,僅奪走她嫡,雖然是庶出,但顧南星,她便是實際的姐的地位,更走父親和祖母的寵愛!
她絕允許!
“娘,您說怎么辦?”
顧巧蓮眼閃過絲厲。
茶近她耳邊,壓低聲音,語速飛:“她剛回來,公爺和夫對她定是又愧疚又生疏。
尤其是公爺,重規矩統!
待兒她進府,按規矩,她這個妹妹的,得給姐姐敬茶!
這就是機!”
“敬茶?”
顧巧蓮眼睛亮。
“對!”
茶眼閃爍著算計的光芒,“你親去奉茶。
記住,要表得溫婉恭順,姐妹深。
然后……”她的聲音壓得更低,帶著絲冷,“‘’把茶盞打,滾燙的茶水潑到她身,潑臉,讓她當眾出丑,燙傷了更!
公爺厭惡舉止失儀、當眾鬧笑話的!
只要她失態,公爺對她那點薄的愧疚,立刻就變厭棄!
夫再疼,也堵住悠悠眾!”
顧巧蓮領,嘴角勾起抹惡毒的笑意:“兒明了!
娘,兒定‘’給這位長姐敬茶!”
鎮公府,正廳,燈火輝煌,亮如晝。
顧清誠端坐主位,面沉肅。
崔悅坐他首,眼睛依舊紅腫,目光卻刻也離地黏顧南星身。
顧南星則被安排坐崔悅對面的首位置,姿態隨意地靠著椅背,把玩著腰間那枚起眼的“腰帶扣”(驚鴻軟劍的偽裝),對廳壓抑的氣氛和周圍仆役打量的目光若睹。
廳氣氛有些凝滯。
顧清誠似乎知該如何,崔悅則是有言萬語卻知從何說起,生怕說錯話又惹兒。
就這,廳來陣佩叮當的輕響,伴隨著個嬌柔婉轉的聲音:“兒巧蓮,聽聞長姐歸家,來拜見!”
話音未落,個身著鵝撒花襦裙的,裊裊地走了進來。
她身姿窈窕,面容姣,柳眉杏眼,肌膚皙,臉帶著恰到處的、溫婉又帶著點怯生生的笑容,正是顧巧蓮。
她身后跟著個端著紅漆托盤的丫鬟,托盤著個致的青茶盞。
顧巧蓮蓮步輕移,走到廳,對著顧清誠和崔悅盈盈拜:“兒給父親、母親請安。”
聲音甜,姿態恭順。
顧清誠到這個向乖巧懂事的兒,臉稍霽,點了點頭:“巧蓮來了。”
崔悅此刻滿滿眼都是顧南星,對顧巧蓮只是淡淡地“嗯”了聲。
顧巧蓮暗恨,臉笑容卻越發甜。
她轉向顧南星,眼迅速蓄起層水光,帶著濃濃的“孺慕”之,聲音哽咽道:“這位……便是長姐了吧?
巧蓮……巧蓮終于見到長姐了!
長姐受苦了!”
說著,竟似要落淚來。
她這副姐妹深的模樣,演得意切,若非顧南星早己洞悉她的底細,恐怕也要被這湛的演技騙過去。
顧南星饒有興致地著她表演,嘴角噙著絲玩味的笑意,沒有接話。
顧巧蓮見她語,冷笑,面卻越發恭謹。
她示意身后的丫鬟前,己則伸出纖纖,親端起了那杯熱氣的茶。
“長姐,”她捧著茶盞,躬身,將茶盞舉到顧南星面前,姿態謙卑至,“妹妹初次拜見長姐,按規矩,當以茶敬之。
此乃的雨前龍井,請長姐……啊!”
就茶盞即將遞到顧南星邊的那刻,顧巧蓮突然發出聲短促的驚呼!
只見她腕猛地,那盛滿了滾燙茶水的青茶盞,竟脫而出,首首地朝著顧南星的胸潑去!
事發突然!
滾燙的茶水空劃出道水,眼就要潑到顧南星身!
“星兒!”
崔悅嚇得魂飛魄散,失聲尖!
顧清誠也猛地站起身,臉鐵青!
廳的仆役們更是發出片驚呼!
然而,就這光火石之間!
顧南星卻并未驚慌失措地躲避,甚至身都沒有離椅背!
只見她端坐的身姿依舊慵懶,只是搭扶的右,如閃般抬起!
沒有清她是怎么動作的!
只聽得“啪”聲其輕的脆響!
那眼就要潑到她身的茶盞,仿佛被只形的穩穩托住,空詭異地停滯了瞬!
隨即,顧南星腕其巧妙地向,引!
嘩啦!
那滿滿盞滾燙的茶水,連同那只價值菲的青茶盞,如同被賦予了生命般,空劃過個優的弧,準比地……潑回了顧巧蓮己的身!
“啊——!!”
聲凄厲到變調的慘,瞬間響徹整個廳!
滾燙的茶水,毫保留地潑了顧巧蓮挑選的鵝襦裙,瞬間浸透,更有部濺到了她露的腕和脖頸,嬌的皮膚瞬間被燙得紅,甚至起了水泡。
顧巧蓮被燙得原地跳腳,哪還有半剛才的溫婉端莊?
她忙腳地拍打著身的茶水,疼得眼淚鼻涕起流,妝容也花了,頭發也了,狽堪!
“妹妹!”
顧南星此才慢悠悠地站起身,臉帶著恰到處的“驚訝”和“關切”,聲音卻清晰比地入每個耳,“你這是怎么了?
得這么厲害?
年紀輕輕就得了帕森?
還是說……”她拖長了語調,眼陡然變得銳如刀,帶著洞悉切的冰冷,“這茶太燙,你端穩?
或者……是這茶加了什么該加的西,讓你虛了?”
她的話,如同冰錐,刺入顧巧蓮的底!
顧巧蓮的慘聲戛然而止,她猛地抬頭向顧南星,眼充滿了難以置信的驚恐!
她怎么知道?
她怎么可能知道?
顧南星卻給她反應的機,她前步,居臨地著狽堪的顧巧蓮,嘴角勾起抹其惡劣、其缺的弧度,始了她的“毒舌”表演:“嘖嘖嘖,這燙的,紅彤彤的,跟煮了的蝦子似的。
妹妹啊,是我說你,你這演技,還是欠點火候啊。”
“想陷害我?
用這么拙劣的段?
潑茶?
還是滾燙的?
你是覺得我傻,乖乖坐著讓你潑?
還是覺得座的都是瞎子,出你那點思?”
“哦,對了,你是是覺得,只要我當眾失態,被燙得尖跳腳,或者惱羞怒打了你,就能讓公爺厭棄我?
讓夫難堪?
順便再襯托你這朵‘受欺負’的花?”
顧南星每說句,顧巧蓮的臉就,身就得更厲害。
“讓我猜猜,這主意是誰給你出的?”
顧南星的目光如同探照燈,掃過顧巧蓮慘的臉,“是你那個出身‘雅’、‘溫婉賢淑’的姨娘,茶吧?”
“茶”二字出,顧清誠的臉猛地變!
崔悅更是瞬間攥緊了拳頭,眼噴火!
“也只有她那種地方出來的,才能想出這么得臺面的段。”
顧南星的聲音帶著毫掩飾的鄙夷,“怎么?
青樓多了爭風醋、潑酒撒潑的戲碼,就以為這招公府也能用?
妹妹啊,是姐姐說你,跟這種‘娘’學,你這格局,也就指甲蓋那么了。”
“你……你血噴!”
顧巧蓮又驚又怒又怕,燙傷的疼痛加被當眾揭穿的羞憤,讓她幾乎崩潰,尖聲反駁,“我沒有!
我只是……?”
顧南星嗤笑聲,打斷她的話,“你當我是歲孩?
還是覺得公爺和夫眼瞎盲?”
她忽然伸出,如閃般捏住了顧巧蓮的巴,迫她抬起頭。
顧南星的指冰涼,力道卻得驚,顧巧蓮只覺得巴像是被鐵鉗夾住,劇痛比,根本法掙脫。
“著我的眼睛!”
顧南星的聲音帶著種奇異的魔力,她的眸深處,仿佛有星河流轉,攝魄,“告訴我,這茶,是是你故意潑的?
是是茶指使你的?
是是想讓我當眾出丑,燙傷我,讓公爺厭棄我?”
顧南星的力(結合了相面術和點點攝魂技巧)壓迫,顧巧蓮只覺得頭腦片空,瞬間失守!
她著那仿佛能透切的眼睛,的恐懼攫住了她,讓她由主地脫而出:“是……是!
是娘讓我這么的!
她說……她說只要讓你當眾出丑,燙傷你……父親就討厭你!
夫也難堪!
我……我就能……”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被聲暴喝打斷!
“住!”
顧清誠臉鐵青,額角青筋暴跳,猛地拍桌子站了起來!
他向顧巧蓮的眼,充滿了震驚、失望和滔的怒火!
他萬萬沒想到,己向認為乖巧懂事的兒,思竟如此惡毒!
更沒想到,這切的背后,竟然是他寵愛了多年的茶指使!
崔悅更是氣得渾身發,指著顧巧蓮,聲音因為憤怒而顫:“你……你們母……毒的腸!
我的星兒剛回來,你們就容她!
竟敢用如此作的段!”
廳片死寂!
所有仆役都嚇得瑟瑟發,恨得把頭埋進地!
完了!
這的捅破了!
顧巧蓮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己剛才說了什么!
她臉瞬間慘如紙,渾身癱軟地,驚恐地著暴怒的父親和嫡母,又臉玩味冷笑的顧南星,的恐懼和絕望瞬間將她淹沒!
“……是的!
父親!
母親!
是她!
是她用了妖法!
她迷惑了我!
我說的是的!”
顧巧蓮語次地哭喊起來,試圖挽回。
“妖法?”
顧南星松,嫌棄地掏出方雪的帕子擦了擦指,仿佛沾了什么臟西。
她將那帕子隨丟地,居臨地著哭得梨花帶雨(是涕淚橫流)的顧巧蓮,嘴角那抹缺的笑容越發明顯:“妹妹,飯可以,話可能說。
什么妖法?
我這‘以服’,懂懂?
哦,意思,我忘了,你跟你那姨娘學的,概只懂‘以茶服’吧?
可惜,技術太差,把己給‘服’了。”
她慢悠悠地踱步到主位前,對著臉鐵青的顧清誠和氣得說出話的崔悅,聳了聳肩,臉辜:“公爺,夫,你們也到了。
我這剛進家門,板凳還沒坐熱呢,就有迫及待地給我‘見面禮’了。
還是這么份……滾燙的‘禮’。”
她頓了頓,目光掃過癱軟地、瑟瑟發的顧巧蓮,語氣陡然轉冷:“來,這鎮公府的水,比我想象的還要深,還要渾啊。”
顧南星那句“水深且渾”的評價,如同后根稻草,徹底點燃了顧清誠和崔悅壓抑了八年的怒火與愧疚!
“孽障!”
顧清誠的暴喝如同地驚雷,震得整個廳嗡嗡作響!
他猛地站起身,的身軀散發出駭的壓,那張剛毅的臉,此刻布滿了鐵青的怒,額角青筋突突首跳,眼銳如刀,刺向癱軟地的顧巧蓮!
他征戰沙場多年,伐斷,厭惡的就是這種齷齪、得臺面的段!
更何況,這段竟然是用他剛剛尋回的、虧欠了八年的親生兒身!
這簡首是赤地打他顧清誠的臉!
踐踏他鎮公府的尊嚴!
“顧巧蓮!
你的膽子!”
顧清誠的聲音低沉而冰冷,帶著雷霆般的怒火,“竟敢眾目睽睽之,用如此作的段陷害嫡姐!
思如此歹毒,簡首枉為我顧家血脈!”
他指著顧巧蓮,指因為憤怒而顫:“滾燙的茶水!
潑向你的親姐姐!
若非南星身敏捷,此刻受傷的就是她!
你年紀,腸竟如此毒!
是誰教你的?
是是你那個‘’姨娘?”
“公爺!
公爺息怒啊!”
顧巧蓮被顧清誠的怒火嚇得魂飛魄散,也顧身的疼痛和狽,連滾爬爬地撲到顧清誠腳邊,抱住他的腿,涕淚橫流,哭得肝腸寸斷,“兒冤枉!
兒冤枉啊!
兒的是故意的!
是……是那茶盞太滑了!
兒沒拿穩……兒絕害長姐之啊!
父親!
您要相信兒!
兒向是敬重父親,怎出這等事來?
都是……都是長姐!
是她!
是她用了妖法迷惑兒!
兒才胡言語!
父親!
您要明察啊!”
她哭得梨花帶雨,聲音凄婉,試圖用貫的柔弱姿態喚起顧清誠的憐惜。
她知道,父親雖然嚴厲,但對她這個“乖巧懂事”的兒,向來是有疼愛的。
只要咬死是意,再推到顧南星“妖法”頭,或許還有生機!
然而,她低估了顧清誠此刻的怒火,更低估了顧清誠那份對顧南星遲來的、沉重的愧疚!
“住!”
顧清誠腳將她踢,力道之,讓顧巧蓮痛呼聲,滾倒地。
他眼沒有絲毫憐惜,只有冰冷的失望和厭惡,“還敢狡辯!
還敢攀誣你長姐!
什么茶盞太滑?
什么妖法迷惑?
你當本公是瞎子聾子?
你剛才親承認的話,場所有都聽得清清楚楚!
是茶指使你的!
是你想害南星出丑!
鐵證如山,你還敢狡辯?”
他越說越氣,胸膛劇烈起伏:“本公是瞎了眼!
竟被你們母蒙蔽了這么多年!
個出身卑賤,術正!
個似溫婉,實則蛇蝎腸!
竟敢謀害嫡姐!
來!”
“!”
廳立刻有親衛應聲。
“將這個孽障給我拖去!
關進祠堂!
沒有我的命令,誰也許她出來!
讓她反省!
跪祖宗牌位前,想想己到底錯哪!”
顧清誠的聲音斬釘截鐵,容置疑。
“!
父親!
要啊!
兒知錯了!
兒的知錯了!”
顧巧蓮聽要關祠堂,嚇得魂飛魄散。
祠堂冷潮濕,跪祖宗牌位前思過,那滋味比打她頓還難受!
她掙扎著還想撲過去求饒。
“拖去!”
顧清誠都她眼,厲聲喝道。
兩名親衛立刻前,毫憐惜地架起哭嚎掙扎的顧巧蓮,拖死狗般將她拖出了廳。
凄厲的哭喊聲漸漸遠去,終消失回廊深處。
廳死般的寂靜。
所有仆役噤若寒蟬,連呼都翼翼。
崔悅此刻也站了起來,她走到顧清誠身邊,著被拖走的顧巧蓮,眼沒有絲毫同,只有滔的恨意和后怕!
她轉向顧南星,聲音因為動和憤怒而顫,帶著哭腔:“星兒!
我的星兒!
你沒事吧?
嚇死娘了!
那個毒婦!
那個毒婦!
她們母……她們母竟然敢……敢這樣對你!
娘……娘恨得撕了她們!”
她緊緊抓住顧南星的,仿佛生怕她再受到絲傷害,眼淚又止住地流來,“是娘沒用!
是娘當年沒能護住你!
讓你被那毒婦害得流落八年!
如今你回來了,她們還敢……還敢……”崔悅泣聲,的愧疚和憤怒幾乎將她淹沒。
她恨茶!
恨顧巧蓮!
更恨己當年的軟弱和能!
顧清誠著妻子如此動,又著顧南星那始終靜的臉,那份愧疚感更是如同潮水般涌頭。
他深氣,壓怒火,走到顧南星面前,聲音帶著絲易察覺的干澀和……從未有過的溫和(對他而言):“南星……是為父……管教嚴,讓你受委屈了。
你,此事,為父定給你個交!
絕輕饒了她們!”
他用了“為父”這個稱呼,試圖拉近關系。
但顧南星的反應,卻讓他頭又是沉。
顧南星由崔悅抓著己的,沒有掙脫,但也沒有回握。
她只是靜地著眼前這對緒動的父母,眼清澈,仿佛剛才那場鬧劇的主角是她般。
聽到顧清誠的話,她甚至輕輕挑了挑眉,嘴角勾起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目光轉向被拖走的方向,語氣帶著種事關己的調侃:“委屈?
還吧。
這種程度的‘把戲’,衍宗,連剛入門的師妹都懶得玩。
太低級了,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她頓了頓,著顧清誠和崔悅臉那混雜著憤怒、愧疚和絲尷尬的表,慢悠悠地補充道:“過,公爺……哦,父親,”她似乎才想起改,語氣卻沒什么變化,“您剛才說‘管教嚴’?
這話我聽著怎么有點怪怪的?
顧巧蓮妹妹,她姓顧,是您鎮公府的姐,對吧?
她從您眼皮子底長,受的是公府的教養,對吧?”
她歪了歪頭,眼辜又帶著點犀:“那她今出這種事,您說‘管教嚴’……這意思是是說,她變這樣,是您和夫沒教?
還是說……是跟她親娘學的?”
“這……”顧清誠被問得噎,臉頓有些難。
他剛才那句“管教嚴”是謙,也是表達歉意,可被顧南星這么解讀,味道變了!
仿佛承認己教方,或者……暗示茶才是罪魁禍首?
崔悅也愣住了,知該如何接話。
顧南星卻管他們,顧地說了去,語氣輕松得像點評氣:“其實吧,我覺得這事兒也能怪你們。
畢竟,龍生龍,鳳生鳳,鼠的兒子打洞。
這‘根兒’正,苗兒能到哪兒去?
對吧?”
她意有所指地笑了笑,“有些啊,骨子帶的劣根,后再怎么裝,也掩蓋住那股子……嗯,你們懂的。”
她這“缺”至的“安慰”,簡首是顧清誠和崔悅的傷撒鹽,還順便把茶的出身(青樓)又拎出來鞭尸了遍!
顧清誠的臉陣青陣,胸堵得慌。
他既覺得兒說得刻薄難聽,卻又法反駁!
顧巧蓮今的所作所為,和茶的“溫婉賢淑”形了何等諷刺的對比!
這讓他對茶的信和寵愛,次產生了的動搖和……難堪!
崔悅則是又氣又疼,她緊緊握著顧南星的,哽咽道:“星兒,你別說了……是娘……是娘當年引入室……行了行了,”顧南星終于抽回了己的,從袖掏出方干凈的帕子,遞給崔悅,“擦擦吧,夫。
眼淚解決了問題,還容易長皺紋。
為了這種哭,值當。”
她目光掃過片藉的地面(打的茶水、破碎的茶盞、顧巧蓮掙扎留的痕跡),以及廳噤若寒蟬的仆役,后落顧清誠身,語氣恢復了那種帶著點疏離的靜:“父親,夫,我今也夠熱鬧的了。
我這剛回來,風塵仆仆的,也挺累的。
要,我先去休息?
至于那位……嗯,‘管教嚴’的妹妹,還有她那位‘根兒正苗紅’的親娘,該怎么處置,你們著辦?
我相信,以公爺的英明武,定給我這個‘失而復得’的兒個‘滿意’的交,對吧?”
她意加重了“滿意”二字,眼靜,卻帶著種形的壓力。
顧清誠被她得頭凜,那眼,仿佛能穿透,讓他這個經沙場的公爺都感到絲。
他深氣,沉聲道:“這是然!
你先去休息吧。
松林苑己經收拾了,是你母親意為你準備的院子。”
“松林苑?”
顧南星挑了挑眉,似乎有點興趣,“行吧,聽著比‘狗尾巴草苑’點。
那我就先告退了。”
她說完,也等顧清誠和崔悅再說什么,對著他們隨意地點了點頭,便轉身,眾復雜難言的目光注,施施然地朝著廳走去。
那背,依舊挺首,灑脫,仿佛剛才那場針對她的風,過是拂過她衣角的粒塵埃。
崔悅著她離去的背,張了張嘴,想說什么,終卻化作聲奈的嘆息,眼淚又涌了來。
顧清誠則站原地,臉沉如水。
他望著顧南星消失的方向,又了片藉的廳,后目光落顧巧蓮被拖走的方向,眼變得比銳和冰冷。
交?
他當然給個交!
個讓所有都滿意的交!
他猛地轉身,對著廳厲聲喝道:“來!
去清荷院!
把茶給我‘請’過來!
立刻!
!”
“是!
公爺!”
親衛統領聲應諾,聲音帶著肅之氣,轉身步離去。
廳,氣氛再次降至冰點。
所有都知道,更的風暴,即將來臨。
而這場風暴的,正是那位似溫婉害的茶姨娘。